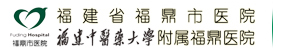在浙江文成,有一道让我让我至今仍思念不已的茶,当地人称之为“白落地”。 一次在一个Q群上和朋友们聊起这个名,一位诗友煞有介事地把它等同于“白兰地”,心中竟有种受到亵渎般的屈辱,脱口便骂到:俗不可耐!
白落地,多么诗意的名字!
那日,在文成,认识了一帮满身“酸臭”、“迂腐”的文友,他们口吐莲花,纯粹而诗意地活着,他们奔前跑后,带我们走红枫古道、刘基故里……
那日,文成的文友在酒馆摆了一桌的酒菜,我的眼睛一直锁定在服务员手中的那壶白落地上。
那是一壶怎样的茶呀! 一个酒店常见却比平常酒店干净透明的玻璃水壶,盛满了文成不受污染的泉水,水中袅袅娉娉地摇曳着几株不知名的植物。那植物似乎柔弱无骨,简直尤物。我一直盯着它如蛇一般在水中四处游走、缠绕,极尽缠绵又极力舒展着,绿得一尘不染。几粒红得精美绝伦的枸杞浮在水面,配合着植物的节奏,无声地跳跃着。盛一杯捧在手心里,那精致的红纯粹的绿让我仿佛捧住了春天,让我不忍心把它喝下去。
入口后的白落地让我再次惊奇。
清淡,润滑,若不是细细品尝几乎感受不出它的味道。依然是春天,是田园,是小径,是竹林,是心中那片不曾被打扰的童年圣地。那里有奶奶的身影,有我童年蹲在田头一株一株挑选用来喂兔子的青草的气息,有许多不曾也不敢提起的欢乐和幸福的记忆。那一刻,当茶水顺着咽喉缓缓滑下时,心中仿佛有春风吹过。仿佛泪滴在杯子里。
那日问遍了文成的那些朋友,没有人知道白落地的真正学名叫什么,只说清凉解毒养颜,只说可以入茶入汤,只说生命力旺盛,只说文成的乡野田间随处可见。
回来后,百度了很久依然没有找到关于白落地的任何正式介绍,却不小心翻到了一篇关于白落地的感人报道,说的是一位母亲靠卖白落地培养了三个大学生的故事。故事曲折感人,让人不忍猝读,也因此让我明白了白落地在文成人心目中是怎样的位置。在我眼里,它和我认识的文成文友以及那位母亲一样坚忍,一样纯粹,一样值得敬佩。
同行的白荣敏老师说:这名,以后归我了!我的笔名从此就叫“白落地”。幽幽的,有句话很想对白老师说:其实我也想要。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