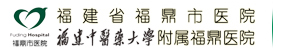上个月末,我与科室的两位心理师去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参加为期三天的巴林特小组培训,收获颇丰。现将三日所学及心得归纳如下,与诸位同仁分享。
巴林特小组是由精神病学家、心理分析师Michael Balith和社会工作者Eind Balith与20世纪50年代在英国伦敦创建。1969年第一个巴林特协会在伦敦成立,1972年国际巴林特联盟成立,1982年开始成为英国全科医生皇家学院,必修课程,它还是美国、德国住院医师课程,澳大利亚全科医学师资培训内容。我国巴林特小组的鼻祖是上海同济医院精神医学专家吴文源教授,2005年-2009年在吴文源的Aisa-link项目中引入了巴林特小组工作形式,2011年CBF(中国巴林特联盟)在北京成立,而后在中国一线城市开花,而目前在上海各大医院,中山,同济,精总每个月都会开展一至二期的巴林特小组的活动。
为什么在中国需要巴林特?为什么医院医护工作者需要巴林特?它的魅力在哪里?它又会给我们医护工作者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众所周知,我国是个人口大国,医护人员短缺历来是个凸显严峻的问题,在高负荷运转下,医患关系相对紧张的医疗环境中,医务工作者在面对现代生活压力(工作竞争,快餐文化的饮食方式,流行追求、物质虚荣心的消费方式,狭窄思考,以自我利益为中心表达的人与人交往的方式,知识爆炸和广泛的社会互动的信息传媒还有莫名的情绪压力)同时来自于自己职业角色压力,很容易出现职业倦怠,达到倦怠标准的是74%,轻度倦怠状态34/3%,中度倦怠程度34/2%,高度倦怠5.5%,甚至部分人群抑郁、自杀。近半数人员在工作中人际关系疏远,缺乏成就感和胜任感,感到生理,情感资源过度消耗。有的人会得过且过,甘于平庸,有的人心比天高,命比纸薄。面对这种压力,这种负面情绪该怎么办?谁来合理化地处理医护人员的压力?这里我引用参加过巴林特小组的医务人员的话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一:“参加巴林之后我可以识别负面情绪,疏泄垃圾情绪,训练积极情绪,保持良好情绪”二:“参加巴林之后,可以识别,理解,处理复杂的情绪反应了”
三:“参加巴林之后能正确的看待压力,学会压力应对,适当的压力是良性的,可以激发人的许多潜能让我更懂得学习,去开发潜能,希望自己成为丰富充满经验的专家”
这只是巴林特小组带给我们的其中一点。
巴林特小组的目标是:
有助于强化医患之间的联盟,使医生也具有治疗作用;更好地理解患者;解决问题的简便方法;利于识别医生自身对患者的情感(反向移情);培养敏锐的倾听能力;帮助医生放松,以防止医生“耗竭”;医生会发现新的视角,消除医生盲点,形成分析型思维方式;更加意识到自身对患者的影响;可能对医生的人格产生轻微的但是重要的改变。
巴林特小组讨论的主题最主要的是:
医患关系,它不是案例讨论,它的特点之一就是不给出问题的答案和解决问题的建议,而是就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与患者、同事、其他人员发生的关系进行整理和思考,以多角度思维去理解他人和自己。
巴林特小组的形式是:
由一位经过培训的组长带领,一般由8-12名医生围坐在一起,俗称“金鱼缸”,讨论在处理病人过程中遇到的难题,识别和纠正医患关系中出现的问题。
小组里的角色分工:
小组组长,病例报告者,其他人员(观察和反馈者)
而我真正领悟到巴林特小组的以人为镜明得失是通过这次培训我作为一个病例报告者报的一个病例,从中体察到它的内涵与魅力。相信每个医生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都会有碰到亲朋好友介绍的病人前来求医,正像每个人应对压力模式不同,人们处理各种各样事情的行为模式也是不同。我有个病例是我最小叔叔的好友,我叔叔很疼我,而这个人是他的好友,在去年的意外一次胃出血后反复出现洗手,看到什么东西都害怕,担心它脏,脑子里反复出现想掐死自己孙女的念头,明知道没必要但控制不了,精检中存在强迫思维与强迫动作。诊断是:强迫性障碍。治疗方案是药物治疗与心理治疗。用利培酮每日4mg盐酸氯米帕明每日200mg.结合暴露预防反应,系统脱敏疗法,厌恶疗法,CBT。患者的白天功能基本恢复,晨起夜晚还是洗手时间约二十分钟。有时还会出现担心掐死其孙女的强迫思维,患者还出现药物副作用锥外系反应震颤。把这病例请教过湘雅医院的两位教授,教授的意见是强迫症属于难治性神经症性障碍,治疗方案没什么问题,关键的是这个量更需要关注的是副作用的问题。患者也曾经求诊温州康宁医院,效果更不理想。我也明白医学是不完美的科学,有时候在不能痊愈的情况下,更多的是让患者明白疾病性质,接纳,带着残余症状生活与工作,但是每当接到患者妻子电话是我还是会有种无力感,作为一名医生面对疾病的无力感,甚而想到如何面对我叔叔。带着这些情绪与困扰,我报了这个案例。当我退出金鱼缸,听小组其他成员代入我的角色进行发言时,我顿然有感悟,一:我与我叔叔必须有个交谈,让他知道强迫症的难治性,让他明白他的侄女虽然从事精神科诊疗工作29年,但她只是医生,不是超人。二、小组成员代入角色的发言让我看到我曾经忽视的一点,为什么一场突然发病后的洗手,这种洗手的背后原因是否来自于对死亡的深深恐惧,每次的来访都有个焦虑的妻子,而伴侣的焦虑是否加重患者的焦虑?从而助长他的洗手时间?在病历上我是否存在思维盲点?我还可以有治疗上的空间。以巴林特其他小组成员为镜明得失,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我想这该是巴林特小组的魅力吧。 (心理精神科 易东晓)